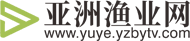那些真正的先生们说学问,都不“高耸”。
刘先生是大学一年级时给我们讲古典文学的。如同我们很久没有在教室里端坐过,他应该也很久没有站在讲台上了。早过了退休年纪,眼睛里已是老人般光晕,可是课讲得好啊!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一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大大的教室里,他讲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,窗外是盛开的栀子花。
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大学生,听着一个老先生讲这些很久前的文学和历史,并没有什么比较,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课!他是一个大学先生!
他没有讲义,手上不拿书,不在黑板上写字,我们全听得懂。全喜欢听。全记得住。喜欢记笔记的同学都记啊记,心里是活蹦蹦的开心、明亮、充满专业希望,还有栀子花的香味。
刘先生喜欢这些久远故事中的谁,不喜欢谁,都直接说出,个性得很,也天真、幽默,眼中的老年光晕闪出一下的是孩子的笑。
每次下课,由东部校园往西部校园走,刚才的课堂都被我们端在一路的话里,一直端进寝室和餐厅。
刘先生以前在别的大学当过老师,也当过我们大学的系主任,但他后来是以讲师退休。学校一直劝他申请一下当教授,他摇摇手,不当了,不当了。
他穿布鞋,大步走路,身子笔挺,不东张西望。
后来的校园里不再有“不当了”“不当了”这样的精神和人了,刘先生的故事是一个结束。
张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。名气很大,威望很大。站在他树下的人不少。他当系主任,待人都客客气气,绿荫般温和,给人提建议也是客客气气。
我那时多年轻,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论文答辩结束。经过二楼系里的走廊,他客客气气喊我,然后建议说,以后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应该肯定一些,不要出现“可能的”字眼。
我竟然年轻嘴快,立即不同意,说,研究怎么可能都是肯定的,不是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吗?
张先生说:“我只是建议,供你参考。”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的怒。
他身后正好跟着几个他的学生,也都是老师,每一个的资格都在我之上。集体都愣了,四射的惊讶。
离开走廊后,有两个分别找到我说,你怎么这样对张先生说话?
我不以为然地说:“我不同意啊!”
过了两天我有些后悔了,也有些担心。
就问到了张先生家里的电话,犹豫着还是在晚上拨通了他的电话,我说,张先生,对不起啊,我没礼貌,不懂事,顶撞了你,你别生我的气,你千万别生气啊!
张先生笑嘻嘻地说,不会的,不会的,学术都是有自己想法的,你不要有顾虑……后来,每次见到张先生,打招呼时心情里都会有亲近的美好,他的学术弟子多,我是语言学专业之外的,但真正的先生,树荫都是一个大的蓬盖,我后来对人提起张先生,都是说“我们的张先生”,我会对人说起自己的年轻嘴硬少修养,说起打完电话后坐在灯下松弛的发呆,这不是一件大事,但我把它当成一件不小的事来说,因为一件事情在我心里撑开得有多大就有多大,我还会对人说张先生喜欢喝的五加皮,我也专门买了喝过,它的颜色像玛瑙一样……
何先生一直研究中学语文,是语文教学的真名家,住在校园的音乐新村里,我刚毕业时被分配了一间小小的宿舍房,在他家那幢小楼的对面,隔着一片空地,长着几棵树,站在窗口看得见他的进进出出,翩翩风度,像一个会走动的知识,像特别标准的语文。他独自走在路上也是有笑容的,没有人迎面走来,他却是彬彬有礼地走去,风度翩翩,彬彬有礼,像是他的世界形象。
他被称为大学里最像教授的教授,是教授的经典模样。
有一个学期,我被安排在他的教研室参加政治学习,坐在旁边听大家说话,沐浴何先生的世界形象,我在写作里几乎不使用“沐浴”这样的词,嫌弃用得太多了,可是现在只想用它,因为那的确是标标准准的沐浴,整个身心笔直端坐,眼前耳边尽是何先生的温良韵味。
在校园里看见他很知识很语文地走来,我都会站立原地等着,不愿意错过了喊他一声,问候一下,他更是笑嘻嘻地迎着我,也喊我一声,他的上海口音和语气,很像上海菜里的这一小碟,那一小盘,他说话从不用大碟子的,永远不会铺满,像一篇篇编制得最细致、简明的课文,供人学习母语的基础和韵律,我偶尔问他一点语文上的事,他也都是最语文地告诉我,彬彬有礼一小碟,但是足够了。
徐先生一直研究文艺学,是个谦谦知识人,温和得很,神情和语气里都含了笑,话语里多有上海话的“是吗”,说到文艺学上的话题,他每一句话都好听得明白,明白得好听,那时,文艺学里已经流行比欧美更欧美,前现代还没有拎起脚后跟,后现代的脚尖已经伸进来,顶得前现代要赤脚逃开,我问起他,他说,哈哈,是这样的,读读书就知道了。我那时也年轻,也学了用脚尖拱一下脚跟,但是后来懂得点徐先生的哈哈,就也哈哈着不想拱了。徐先生那样的书人,西方和中国的理论学得兼备,他曾经跟着上海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编了多年的权威教材,虽是有“时代性”,但是功夫扎实,自在严谨逻辑中。后来那位文艺理论家的儿子也进了大学,比我低两届,如我弟弟般和我来往,我领着他去见徐先生,换着公共汽车到了徐先生家,我指着问徐先生,你知道他是谁吗?
我说出了理论家的名字,徐先生吃惊得眼圈红了,理论家已经去世十几年,徐先生喊着他儿子的名字:“新跃啊!”
新跃和我一起编着系里的学生刊物《文友》,徐先生当顾问,学生写的文学总是会热情不少,幼稚也不少,徐先生总是说,不错的,不错的,学文学的,写写文学,文学会学得更加有感觉的。
新跃也爱好写。
徐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红学家,我当知青时就总读到他的《红楼梦》文章,熟悉他的名字,但是这时他已经很少说《红楼梦》,他遇过磨难,正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年代写了《红楼梦》文章,以他的口才,温温稳稳的语气、节奏,足够的文艺理论修养,讲起来必然非常好听。
徐先生说理论,还有那些真正的先生们说学问,都不“高耸”。
新跃后来每次从美国回来都去看徐先生。
先生们都还在的,在我的文字间。(梅子涵)